上个月,我带着一份久藏心底的念想,踏上了前往福建诏安的寻根之旅。这个位于闽粤交界的小城,是先曾祖父年轻时生活过的地方。当年,他从这里启程,远渡南洋,家族的命运便在星辰与大海的交汇处悄然改写。
活着的祖祠记忆
诏安,被称作“福建南大门”,却远离喧嚣。这座小城,至今仍完整保留着规模宏大的宗祠家庙群。漫步县城,随处可见飞檐翘角的家庙错落其间,香火未断,仪式尚存。与北方一些仅供凭吊的宗祠不同,诏安的家庙是活着的——老人们在庙前闲话家常,孩童在青石板上追逐嬉戏,古老的礼仪就这样自然地流淌在日常之中。

诏安家庙外观。(图:沈斯涵)
家庙,是血脉的记忆。尽管有人说,这里藏着巨大的文化旅游潜力,但我更愿意它们静静伫立,如一段段未完的家族叙事,被小心翼翼地守护,而不是被消费。对许多新加坡人来说,诏安或许只是地图上的一个名字,但对沈氏族人而言,这里却是原乡,是故事开始的地方。诏安素有“沈半县”之称,而我,此行便是为寻根而来。

诏安家庙内部一隅。(图:沈斯涵)
迷雾中的宗族线索
寻根于我,并非一次简单的回溯。自祖父辈以来,家族与故乡的联系已日渐稀薄。关于先曾祖父的故事,也只留存于墓碑上寥寥几行字:诏安县东城村人。我曾以为,只要来到这里,便能顺藤摸瓜,找到失落的脉络。然而,当真正置身其中时,才发现,那些过往早已如烟水模糊,寻觅远比想象中漫长。

沈氏家庙牌匾。(图:沈斯涵)
通过诏安侨联的微信公众号,我联系上了诏安县委统战部副部长、侨办主任沈林松先生。攀谈之下,我们惊喜地发现竟是同宗族亲。这位深耕侨务工作多年的宗长,不仅为我详细讲解诏安沈氏的源流,还引荐了诏安县书画收藏学会沈耀明会长、侨联主席李炎武先生等前辈。他们带我翻阅厚重的族谱,行走在古老的街巷,渐渐拼凑出家族模糊的轮廓。

作者(左)与沈耀明会长(中)和沈林松部长合影。(图:沈斯涵)
原来,诏安沈氏可追溯至唐初,沈彪将军随陈政、陈元光父子令军入闽开漳,落户漳州,子孙遂繁衍至龙溪、漳浦、诏安各地。沈彪将军后来被尊为“沈祖公”,世代奉祀,香火绵延。千年光阴,枝蔓四散,虽未能厘清自己确切的支脉,但那种血脉相连的温暖感受,已弥足珍贵。

作者给沈氏祖先上香。(图:沈斯涵)
用脚步丈量乡土
在距离县城不远的东城村,我独自缓步。这里,有祭祀沈祖公的家庙,也有供奉历代祖先的宗祠。石径斑驳,古木苍苍。穿行在巷弄之间,我仿佛能看见百年前的先曾祖父,年轻的他,或许也曾在同一片天空下,悄悄筹划着远行的梦想。沈林松宗长一边引路,一边细细为我讲述每一座家庙和宗祠的来历。

诏安东城村。(图:沈斯涵)
这些日子里,我走过了一座又一座祠堂,听闻了一段又一段族人的故事。每一块石碑下,都沉睡着风雨如晦的年代;每一盏微弱的香火背后,都有一个家族跋涉千里的痕迹。在东城村的一隅,我停下脚步,仰望着天边渐晚的光。风从远处稻田吹来,带着微微的泥土气息,像极了南洋雨后的味道。
那一刻,我想起了先曾祖父。想起他百年前离开故土的身影,想起他在茫茫大海上押注未来的勇气。他是否曾回头望过一眼故乡?又是否料想到,他的决定,会让家族在另一片土地上,生长出新的枝叶?

作者寻找曾祖父的足迹。(图:沈斯涵)
如果没有那一场远行,我不会在新加坡成长,我的祖父、父亲不会在新加坡成家立业,而我,也不会成为今天的我。归来,是为了更好地出发。血脉的源头,在诏安;而生命的枝叶,早已在新加坡舒展开来。
带回井水延续缘分
在东城村的老井边,青苔爬满石栏的缝隙。我俯身打水,听见井底传来遥远的回响——那或许是百年前某个清晨,先曾祖父打水时荡开的涟漪,至今仍在时光深处微微颤动。如今,这瓶井水静静立在我的书架上,与沈氏族谱比邻而居。

诏安县城。(图:沈斯涵)
夜深人静时,月光穿过玻璃瓶,在族谱扉页投下晃动的光斑,仿佛东城村的星辰,在轻轻翻阅属于我们的章节。它们,一个凝固着血脉的密码,一个流淌着记忆的微光,在都市森林的一隅,静静延续着跨越山海的对话。
站在时光的交汇处,我终于懂得:所有的远行,都是归来;所有的归来,亦是新的开始。先曾祖父当年带走的井水,早已化作南洋的雨;而我带回的这一瓶,也将在阳光下,静静守护一段跨越百年的缘分。
在一代又一代的呼吸之间,那盏在沈祖公庙前永不熄灭的灯火,依旧在微光中,温柔跳动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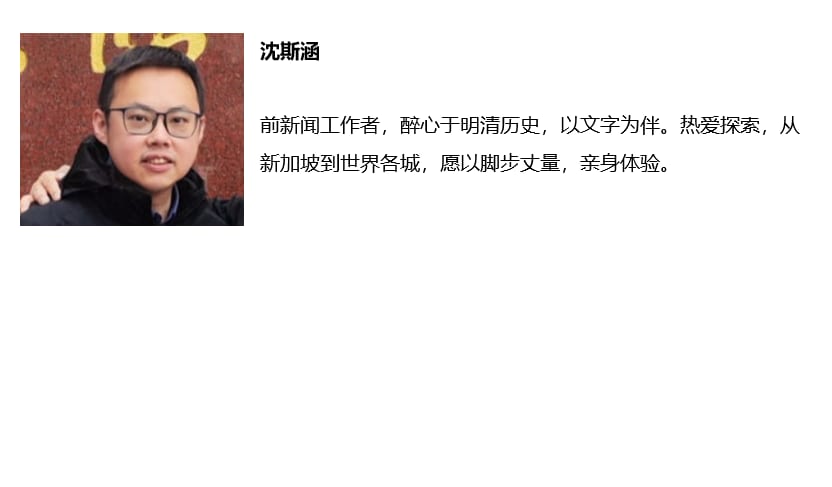
请点击《城市呼吸》系列报道,阅读更多文章。
本文为作者观点,不代表本网站立场。






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