对许多人而言,“诸暨市”这个名字或许并不为人熟知,更遑论隐匿在这座位于浙江,小城郊外山峦之间的斯宅村了。几个星期前,我趁着周末的闲暇时光,走进这个人迹罕至的古村落,试图寻觅历史在这里悄然留下的痕迹。
斯宅村四周青山环抱,碧水萦绕,俨然一片风水宝地。然而,它不仅仅拥有秀丽的自然风光,更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村,时间的足迹可以追溯到唐代,斯氏家族在此定居繁衍。

青山环抱的斯宅村。(图:沈斯涵)
时至今日,村中依然保存着十余座完整的清代古民居。这些古建筑群规模宏伟,保存完好,木雕、石雕、砖雕的装饰工艺,蕴含着浓郁的地域文化特色,是研究江南地区清代民居建筑的珍贵实物资料。

斯宅村依然完好保存着清代古民居。(图:沈斯涵)

斯宅村民居建筑上的雕饰。(图:沈斯涵)
民国才女张爱玲在1946年,从上海前往温州探访胡兰成时,曾短暂停留于斯宅村,并在她的作品《异乡记》中提到过此地,记录下她所见的乡村春节、杀猪场景以及农民的生活细节。这段短暂的停留,也让斯宅村的名字随着她的文字在时光中留存。
那么,为什么在这片远离尘嚣的山野之间,会有如此规模宏大、雕刻精美的建筑群呢?当地的村民解释道,原来他们的祖先数百年前外出经商,功成名就后衣锦还乡,将财富带回家乡,修建这些古宅,以建筑凝固文明,代代相传。也正因为斯宅村地处偏远,城市化的洪流未曾波及,这里的古迹得以完好保存,仿佛时间在此被轻轻按下了暂停键。

斯宅村地处偏远,未被城市化洪流波及。(图:沈斯涵)
正所谓,山水育人,文化润心。斯宅村与其孕育的居民始终是相互滋养的。这里不仅保留着完好的古民居,还延续了传统的生活方式:采摘茶叶、板栗,依然以传统农耕为主,过着自给自足的日子。当然,如今村中的居民大多是年长者,年轻人早已走出这片山谷,前往市区或其他大城市追求梦想与事业。

斯宅村居民剥板栗。(图:沈斯涵)
然而,当我在古宅的长廊中漫步时,仿佛时光就在这石砖间静静流淌。我看见三五成群的村民聚在一起剥板栗,脸上洋溢着闲适的笑容。他们告诉我,这些是祖祖辈辈的手艺,不管外界如何天翻地覆,他们依然守护着这片土地,延续着家族的传承。

斯宅村长廊尽是村民的日常生活景象。(图:沈斯涵)
古宅的整体布局方正严谨,院落、大厅、楼座通过廊檐相连,天井分隔,使得原本相对封闭的格局,依然保持空气的流通。斯氏祖先的智慧,在这些建筑中展露无遗,仿佛每一块砖石都在静静诉说着百年前的故事。

斯宅村廊檐相连,天井分隔,民居住宅的空气流通顺畅。(图:沈斯涵)
当我即将离开斯宅古村时,眼前的景象让我顿生不舍。一条小河从村前静静流过,村民们带着家人在河中戏水,或在桥下悠闲地烧烤,怡然自得的生活,流露着江南水乡的别样情趣。小桥流水人家的画面,在这里以另一种方式诠释着古村的风雅。

斯宅村村民在小桥下的闲适日常。(图:沈斯涵)
我站在斯宅村外,望着那条小河静静流淌,河水映着古宅的影子,似乎连时间也融进了水波里。我忽然明白,这片土地上的一砖一瓦、一草一木,不仅仅是历史的见证,它们更是岁月的沉淀,默默诉说着这里的过去与未来。正如那山中的风声,虽无形,却在岁月的耳畔低语;而那水中的波纹,虽转瞬即逝,却总有几道涟漪久久荡开,不肯散去。

斯宅村村民在河边戏水。(图:沈斯涵)
村民们依旧在河畔谈笑,岁月的更迭仿佛并未在他们身上留下过多的痕迹。而我,在这山水间,仿佛也被这份安宁和谐感染。斯宅村远离尘嚣,却在静谧中流转着千年的韵律。或许它的故事,并不需要被时间记住,正如这流动的河水,它走向远方,却始终属于这片山谷。
带着这份未尽的感怀,我缓缓走出古村,心中却已然为这片土地的静美留下一隅。斯宅,不仅是一个村落,它更像是一位老者,带着历史的皱纹,静静伫立,等待着有缘人去倾听它的故事。离开了,仿佛我与它的缘分也未曾真正结束,而只是暂时搁浅在岁月的某个节点,等待着下一次的相遇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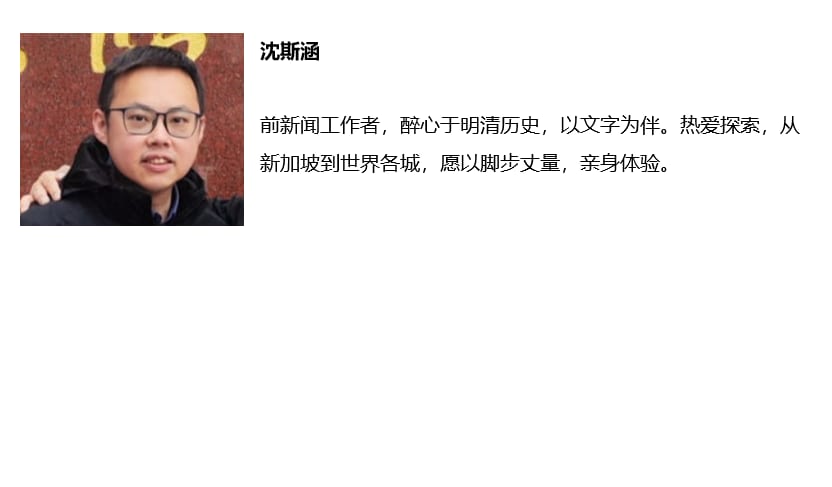
请点击《城市呼吸》系列报道,阅读更多文章。
本文为作者观点,不代表本网站立场。









